
自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的物种而存在以来,第一要务便是生存。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对周遭环境的改变,或大或小,或强或弱。人们可能总是抱持着一种错觉,那就是古时的人们兴土木,垦田地,修河坝,动刀兵时,除了最后一项,都能够做到与自然和平相处。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所有水利工程,都能达成都江堰那样浑然天成的效果,也不是所有田地都如同梯田一样,能够从容融入山水之间。人们要给自己创造生存空间,于是就开垦田地,建造房屋,这无疑需要征伐树林,采挖水井,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以至于多年以来没有树林的平衡的情况下,旱涝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多,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巨大损害。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伴随着对环境的改变,连一般的生物也要遵循这样的逻辑,植物无论在水中还是在陆地,无论是在水中自由漂浮,还是发芽生根直至固沙成土,都有同一个目标,吸收阳光水分、二氧化碳和土壤养分,为自己获得营养,再排出氧气;动物都要寻找食物使自己生存下来,要么像啄木鸟一样啄破树干,使其孳生虫害,然后得以啄食,要么靠着捕猎或者就地取材的方式,捕食猎物或者食用植物茎叶。人类最为特殊,发展到现在,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地区的地貌,甚至是河流走向。
但发展的副作用就在于,其过程伴随着惊人的浪费与损耗,到资本主义时期尤甚。资本主义使我们拥有了电话、路灯,汽车和飞机,它超越了人们经过文化交流和它的最高形式——战争设立的界限,将整个世界拉到一起,原本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路程,现在却只需十几个小时甚至是半个小时不到。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看重的从来都不是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与隔阂的消亡,而只是利润的多寡,工业运转剩余的边角料可以因为成本高昂被丢弃而非被再次利用,造成长时间不可逆的环境污染,残害着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

1.1、工业革命时代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达成的成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工厂、矿场的兴建和扩张,在人类文明尺度的范畴内,彻底地而迅猛地改变了周遭的环境,甚至会因此而随时反噬人类自己。
资本主义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的改变,之前只可能在皇宫旁边的河流见到被成堆倾倒的胭脂水流,现在以一种更普遍、更频繁,也更危险的方式从各个临近工厂和矿基地的水源中出现了——化学品河流,黑炭河流。
甚至可以因为用光了水而断绝河流,因为搬空了整个地下而使人类居住地危如累卵。焦作就是一个大煤矿,从英国资本家在此大兴矿业开始,人们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几乎挖空了这里的地基,几乎抽干了这里的地下水,使得现在的焦作地质岌岌可危,人们的住处就像压在一块脆弱的泡沫板上的重物,承受不起任何突如其来的意外。
而类似的情况,在16世纪的英国就初步显现出来了,那时的人们较为依赖直接获取的木材,但英国的森林资源并不丰富,所以造成了木材的紧缺,这从侧面也反映出,英国因为工业发展的需要,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了,之所以在之后有所收敛不是因为资本家们产生了环保意识,而是因为木材的价格与之前相比可谓是突飞猛进,这可无法使追求利润的商人满足。所以煤炭成为了价格低廉的替代品,矿工这项职业也变得热门了起来。
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可谓天差地别,前者可以跨越人为的界限,堂而皇之地到他国地界去肆意采伐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而贫困的底层群众却会因为一纸“森林盗窃法”,以至于捡拾几根枯树枝便轻易获罪。
1.2、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资本主义在缩小世界的同时,迫使着农村人口成批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于是大量准劳动力,进入了对于他们来说无依无靠的城市环境,与同僚合住成为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在工业革命后,矿工由于其高危险性,工资一般来说会比普通工种要高一些,但这并非我们忽略他们的借口,他们冒着塌方、炸药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为人类社会开采出了宝贵的动力来源,高工资是他们应得的,而不是工业革命前犹如奴隶一般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状态。
但这同样不是为那些人格化的资本辩护的理由,他们对公共卫生的漠不关心,以及工人居住和工作空间,还有工人生命本身的冷眼旁观,都有人亲眼见证和亲笔誊写。
美国的一位叫罗伊斯顿·派克的编辑,他编了一部书叫《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里面详细记录着英国工业革命中,工人阶级遭受的无穷苦难。由于被迫群居,而居住地的基础设施十分差劲,排水和厕所都成了问题,水龙头和厕所的数量都是紧要问题,多达五十户家庭只能共用一间,而且由于排水问题,只留下了臭气熏天而迟迟未被清理的水沟。读者们都应该清楚,没有被及时清理的排泄物都是流行性疾病的安乐窝。
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他们不去清理呢?如果有人问的话,笔者会直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那时矿工的辛劳程度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诸多的妇女和儿童甚至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让我们着眼于事实吧,同一本书的另外几部分记载着,1842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展现了一位叫艾莉森·杰克的11岁女孩作为运煤工的工作流程:从煤层走起,先走一段84英尺的路,然后爬一架18英尺的梯子,走一段时间后再爬上一架38英尺高的梯子,才能到达矿井底下,最后把煤块卸到矿车上。这样从凌晨两点下矿直到下午一点出矿,她要持续工作整整13个小时!而像她这样的童工也不止一人。
成年女工的劳动强度更甚,苏格兰矿场的工作环境极度恶劣,阴暗、潮湿和低矮的人工隧道,灰尘和发酸的化学气体,以及长时间得不到休息的工作强度,无一不在摧毁着女工的健康。甚至怀有身孕的女工也无可幸免,高强度的工作使她们流产甚至当场分娩,而每日的报酬却只有八便士!这是什么概念?在属于维多利亚女王“荣光”的19世纪,1便士的购买力只能买一杯不够为一个工人半天的工作强度提神的咖啡,8便士换来的只不过是仍然不够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温饱的一块牛肉或者一块排骨。
而且同样是由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超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时间,男矿工同样苦不堪言,他们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是疲惫不堪的,以至于“家里的房子上的椽(chuan,四声)木都被蛀虫咬了,偶尔还会掉下虫来”都不曾花时间修缮过。房子的窗户都不怎么规整,通常是用纸糊、破布或者是旧帽子塞住而极少用玻璃,因为根本装不上去;坑洼不平的地板也无人管理,因为根本没有闲暇时间。
以及,仍然是因为工作场所的恶劣和负荷超标的工资强度,工人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进食不规律和被迫饮用煤矿的脏水使工人得胃病,高强度的劳动使工人罹患心脏病,阴暗潮湿的矿井让工人的身体成为风湿的常驻客,以及最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全然是由开采之后产生的灰尘造成的,工人与煤炭打交道,除了吸入别无他法。人身安全全然无处保证,矿井中的瓦斯不仅容易使人中毒窒息,而且具有极其危险的爆炸性,一旦爆炸,再加上矿井排水系统的落后,常常使得多名矿工不幸而沦为残疾人甚至失去生命。
恩格斯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惨状,他曾为此愤然写道:
“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工人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
小修小补处尚且如此,那事关重大的居住场所,工作场地,“五谷轮回之所”,连着最重要之处——工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处于管理盲区便也显得毫不奇怪了。但从来如此,便对么?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此给出的答案,从来都是否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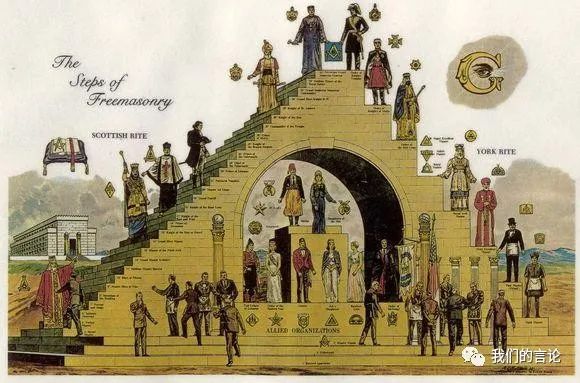
1.3、是天灾,更为人祸
天灾可畏,而人祸更甚。元朝末年的灾荒就是个绝佳的例子,时年无雨,岁大饥,死者相枕藉,生者气无多。元朝官方的救济措施虽然下达了,却只是官方大肆盘剥过后的虚伪施舍罢了(纵然这是元朝出手最阔绰的一次救济)。但即便如此,这虚伪但好歹存在的施舍也让下级官员变成了虚无的施舍,救济粮被他们层层盘剥,到每个灾民手中时,已经所剩无几。
灾民之所以还能有存活群体,那便是因为,当地士绅主动或被迫承担起了救济的责任,取代了基层政府的职能,对元朝政府摆烂以转嫁天灾成人祸的怨恨,也让士绅群体以及广大农民群众与官方更加离心离德,促成了元朝的灭亡。
相应的,如果没有两百年来的资本积累,伦敦也会像巴黎和彼得格勒那样,成为工人阶级不满与怨恨的发源地。1952年12月5日的那场雾霾,人们照常上班,点起煤炉启动机器,向天空排放浓雾黑烟。
今日无风,然而这才是悲剧所在。没有风,雾霾逐渐变成可怖的黄褐色,就这样笼罩在伦敦上空,竟持续了五日之久,泰晤士河航道被迫中断,鸟类经过也会死亡,而身居其中的伦敦市民则首当其冲。这几日,伦敦东区作为工厂的集中地带,工人阶级身体健康深受影响,浓烟久久不散,胸闷和窒息都是小事,造成的不可逆的呼吸系统疾病,后遗症影响深远。没有多少人能够逃离这场五日的灾难,因为人们连对街的景象都看不到,雾灯也丧失了他的作用。
资本家深受其咎,他们的工厂终日排放有害物,终于在这一刻反噬了自己,迫使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在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但如果没有5日后的那场微风,还有4年后的法案,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呼吸道会遭遇何等下场呢?
肺病,硫中毒,以及由此造成的惨死,这些可不在资本主义的负责范围内,只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自己也受到了自然的惩罚,这是他们应得的,但大自然从来没有阻止过他们转嫁祸端的行径,只有工人阶级自己,和他们的急先锋,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才能够达成,否则只是无穷无尽的、麻绳专挑细处断的人间地狱。

2.图穷匕见
在上个世纪美国的股市界有着这样一句俗语——“当路边的鞋匠都在讨论股市的时候就说明股市即将崩盘了”。随着疫情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矛盾的影响,世界市场的整体信心都在摇摇欲坠,经济危机的逼近让资产阶级尽一切可能进行节流。
他们先是把手伸进工人的储蓄中,让他们背上贷款买房生育;在榨干工人最后一丝消费欲望后又把手伸进工人的保障中,延缓他们的退休年龄或减少他们的养老金;在夺尽了工人最后一点明面上拥有的财富后资产阶级又对工人交的税(个税和消费税)中动起了心思,削减公共安全开支让工人承担本该由政府负责的问题。
真是应了这句“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只是现在资产阶级成为了统治阶级,所以工人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只能承担以往双倍甚至更多的压榨了。
2.1野火烧在资产阶级的黑心眼上
美国纽约时报在6月8日报道加拿大野火之蔓延及肆虐,美国政府对加拿大的野火表示慰问,并在文章中对加拿大的救火措施多有褒奖,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表示已经在全国各地部署了数百名士兵协助灭火工作并表示他的政府在考虑成立一个联邦灾害反应机构。
全文避重就轻,只对灾害可能导致的情况和民众受到的影响(还是侧面描写)做了阐述,而对解决方式和加拿大政府应尽的责任没有提及哪怕一字一句。事实上这次野火早在五月和六月就已经发生,新斯科舍省有22000公顷森林被大火烧毁,魁北克有超过150处野火正在燃烧,而有110处无法控制,理由竟然是省政府“没有资源灭火”,整个加拿大陷入野火的包围圈中,仅安大略的野火数量就达到了2022年的两倍之多,其他各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浓烟一度从美国纽约经过华盛顿特区,一直向西到明尼苏达州。在新斯科舍,火灾烧毁了151所房屋,16000名撤离者中至少有4000人可预见的会在未来流离失所。迄今为止加拿大已有12万人被迫逃亡,焚毁面积已达330万公顷,而野火最旺盛的夏季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们请问:这时纽约时报中提到加拿大总理承诺的数百名士兵在哪里?又或者说哪怕他真的部署了数百名士兵,面对数百处野火又有什么应对措施吗?我们再问:联邦灾难反应机构在哪里?什么时候组建好?组建完成后能否应对这次野火?我们最后问:为什么魁北克的省政府没有资源灭火?如果省政府都没有消防预算,部署士兵和联邦灾难反应机构组建的开销谁来承担?如何保证不会又是空口无凭的画饼?
我们遗憾的发现,早在去年安大略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OPSEU)主席JP Hornick就表示缺少23名消防员,而在今年缺口不减反增到了50名消防员。看得出来,加拿大政府在嘴上说的很积极,然而真要应对火灾却一点也不积极。这次野火已经俨然不只是一次自然灾害,而是加拿大政府的一场政治危机,加拿大资产阶级毫无诚意的处理方式只会大大损害政府公信力,而工人阶级将会成为他们作秀的政治代价!
2.2社会主义或野蛮
当一个聪明人开始装傻时,只有傻瓜才觉得他是真傻。是什么让加拿大政府宁愿直面工人阶级的怒火也要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格雷顿·史密斯表示安大略省能够投入更多预算去对抗火灾,但官方的作为立马打了这位自然资源部长的脸。6月7日,安大略省新民主党领袖玛莉特·斯泰尔斯在推特上发文称:“我们不会忘记道格·福特的保守党从安大略省紧急森林消防预算中削减了67%”。在2021~2022年,该省预算2.37亿美元用于紧急森林消防,在野火愈演愈烈的情况下,2023~2024年的计划不升反减至1.35亿美元。
无论道格政府如何狡辩,削减开支的意图都是路人皆知。但新民主党上台就会增加开支吗?当然也不会,因为削减开支是符合加拿大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的,正如法国缩减养老金一样,除非资产阶级不再是统治阶级,否则缩减养老金就是上台的政党的工作,无论他们在野时说了什么。并且加拿大资产阶级可不仅仅在削减开支一件事上获利,在IMT的文章《加拿大在燃烧:社会主义或者气候灾难》中还提到了一个被加拿大政府当局极力否定的事情——世界上最大的88家碳生产公司(其中大多数是化石燃料公司)的产量与中风数量和严重程度成正比,而这又会直接影响西部的野火。在工人阶级燃烧的时候,统治阶级毫无疑问在获利。
肯·斯图宾指出:“我们过去的野火是季节性的,只要过了这个季节就再没有旺盛的野火了。现在我们在一些冬天都会遇到野火,那里没有太多的积雪或降水,即使是在隆冬”,资产阶级政府的短视和逐利让野火逐渐成为了加拿大全年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灾难中流离失所,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流离失所。纵使身后洪水滔天,资产阶级仍可以带上资产逃往他国,被扔下的工人阶级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社会主义。

2.3谁来为工人们说话?
消防员短缺在加拿大并不是偶然现象,他是整个制度下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政府缩减财政,没有预算就无法雇佣消防员,就连现有的消防员都被一再剥削打压。
早在2017年哈利法克斯地区时任消防和紧急情况的负责人肯·斯图宾就一再警告消防预算太小,没有足够的培训材料就更别说消防员了。消防的威胁越发显著的笼罩在每个相关人员的头上,但资产阶级政府的选择是变本加厉:安大略省北部的消防员不再被提供永久合同,相反,消防员只能得到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合同。在结界危机的影响下,加拿大的普通工人(尤其是年轻人)每天有时甚至需要上两种班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消防员面对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则让他们连第二份工作都没有考虑的必要了,然而工资和保障在政府的影响下却完全不成比例,这让招募难上加难。
同时加拿大的许多消防工作都由社区志愿者负责,曾经工人们的经济条件尚可时或消防员拥有永久合同时都会定期去处理森林中的隐患起火物,而如今社区志愿者几乎只剩下了老人。面对如此严重的体制问题,安大略省长道格却大言不惭的表示:“实际上,我对反对派将野火政治化感到震惊。”他没有承诺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要求工人们不要点燃任何营火。政府对消防员没有任何尊重和优待,又将野火意指露营者乃至所有加拿大工人阶级,这更加惹怒了原本就因为政府失责受损最严重的工人们。
灾难面前资产阶级仍然不忘对工人阶级落井下石,谁来为工人们说话?唯有托派们,更唯有工人阶级自己。
(责任编辑:山鹰)